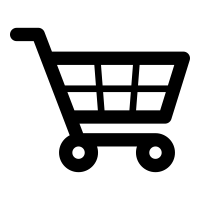沙头往事 第六章 上 (原创天地) 2910次阅读
观看【眉子】的博客----------------------
注:本文的奶奶系指外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
.
第六章 街坊
“吃他娘,喝他娘,死了有街坊。”
这是一种特别横的人说的一种话,就算有个什么不测,还有街坊认得,帮忙收葬。
街坊知根知底。何况象我们那种板壁屋,你不想听壁根子都不行。
.
.
1
我们的紧隔壁,右边一家是异乡人。男的王海生,又高又壮又凶,满脸横肉,不象闽南人,却说一口极难懂的福建普通话。女的肯定是同乡,面目清秀,却苦着脸没有笑模样。大女儿先天兔唇,绰号“豁巴子”,不招人喜欢。儿子年龄很小,但是很宝贝,传宗接代的。
一般外地人都会觉得本地人欺生,就像新移民往往感到受歧视。王海生的办法,是时时处处显示他的凶悍,让别人都知道他是不好欺负的。常常挥舞着扁担想要打人。久而久之,大家都躲着这个远近闻名的恶人,看他来了,早早避开,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他挑水用一对大铁桶,容量是别人的两倍。可是也只出一分钱。
他说话一般都是吼的,粗声大气。瞪着两个眼珠子,张牙舞爪,象要吃你似的,太吓人了。只有他女人敢跟他吵,尖着嗓子,又快又急,说着他们福建话,我们一句都听不懂。女人不摔碗,拿水瓢在铁桶上乱敲。他们吵架,完全是掀翻屋顶的架势,隔壁三家都能听见。也没人敢劝架。王海生手一挥,就把来人划拉开去了。他出手重,揪了女人的头发打。家里大的哭小的叫,简直没法过。
他妈来住过一阵,帮忙带孩子。也又高又壮,但不凶。因为不会说普通话,我们又听不懂她的福建话,零交流。她在家里跟两个孩子说福建话。有一年冬天下雪,她跑出来手舞足蹈指着天上的雪花,嘴里大声说着什么。我奶奶说她没见过下雪。我们都觉得很好笑。他们家奶奶是好人。
.
.
.
2
我们左边隔壁,住着吕爷爷一家。
吕爷爷应该算是我外公同事,灰白头发。清瘦,很普通的老头子,抽烟,每天都要喝酒。一个玻璃的酒瓶子,扁扁的,小小的,揣在怀里,有时候拿出来咪一口。酒喝完了,就要他女儿去杂货铺再打。吃饭的时候,他就不喝那个扁瓶子了,小酒杯,来一盅。
他老婆,在居委会的棕蓬社做事,打“绷子床”。天气好的时候,他们把架子都搬到人行道上面,任人围观。那个“绷子床”相当于现在的席梦思,是正儿八经的卧具,卖钱的。先钉一个四围木头的框子,上面钻很多眼。这一道工序不归吕奶奶管,吕奶奶只管上绷子。用棕搓成的绳子,象织渔网一样在木框子里来回穿插,先织出经纬,斜着交叉又织很多道。每一道都要很大力气绷得非常紧才行。否则人睡上去就凹下去了可怎么办!完工以后那张“绷子床”平平整整真是漂亮极了,任你在上面打滚翻跟头它还是好好生生的,又有一点蹦床的弹性。不过这种床,多睡几年后还是会往下陷的。如果哪根棕绳朽了断了,那就是大问题,很快出现一个洞。吕奶奶他们,好像也帮人修补,总比新床便宜吧,谁不是过日子呢。就象弹棉花,旧棉花弹成新棉花,半斤花弹出八两八,不花太多钱,铁板一块的棉絮重又蓬松暖和。
吕奶奶有个特殊嗜好,吃臭皮蛋。
我们以前吃的皮蛋,外面都糊着厚厚的泥巴和糠壳子。里面的好坏,一点都看不出来。遇到一个坏蛋,只好自认倒霉,白花钱。一般都是稀的,流水,不成形,臭不可闻。扔了可惜,既然她要吃,谁家出了个臭蛋就都给她,免得浪费。当然不要她钱,反正是要扔的。经常到了吃饭的时候,有人巴巴地走好远给她送个臭皮蛋来,一边怨自己运气不好,怎么碰到个臭蛋,吃又不能吃,还白花钱。吕奶奶笑着接过来,难为人家专门跑一趟。
现在想来,她恐怕也是为了不浪费,而且不花钱。有好皮蛋,谁不知道吃好的?
他们的大儿子是工人,很会游泳,横渡长江那种。他用一口废铁锅种了各色太阳花,漂亮极了。放在屋顶的瓦缝间,要搭梯子上去浇水。我老担心那铁锅会溜下来砸到头,可是它稳当得很,尖头卡在两道瓦脊间,刮风下雨打雷扯闪纹丝不动。他把花种屋顶上似乎就是为了防我的,可远观而不可以亵玩焉。
他们家的猫捉了麻雀,亵玩。不吃,叼到我们面前显摆。麻雀一动不动,它就拿爪子戏弄,左拔拔,右拔拔。麻雀动了,它立刻伸爪子按死。不许动。
他们女儿读中学。课余打麻,是我们那一片的打麻能手,人人称赞。
我是他们家常客。两家的大门挨着,跨两道门槛,嗤溜就窜过去了。他们喜欢我去,因为我是他们家小童工。
他们家有一台木头做的打麻机。有些象缝纫机,脚下不停地踩踏板作为动力,手上往一个入口喂麻。机器将麻吃进去后,扭呀扭的,绞成麻线,缠在一个轴上变成个大麻团,这就好了。麻团取下来一个个码好,论斤称,交给居委会换钱。属于来料加工,原麻也是从居委会领的。
原麻大概尺把长,粗细不等。喂麻的时候,一根麻到头了,用另一根麻接上,机器自会把它们绞在一起,成为一根完整的麻线,没有接头。手眼协调,动作要非常快,左手捏一把麻,右手捋着麻将尽的时候,赶快择一根续上。如果机器一直不停地吃麻,效率当然就高。如果老要停下来,就慢。
可是那些原麻,粗的粗,细的细,长的长,短的短。不整齐。除非你先分一遍,将粗麻分成几股,放在案上排好,喂麻的时候一根接一根不停,那才快。否则停一下,拿根麻分半天,那还怎么弄,慢死了。
这时我就派上用场了。让我拿一把麻站在机器旁边,小手分一分粗麻,递给她,她接过去只管往机器里喂。我分的麻细而匀,她踩着踏板轮子飞转,织出来的麻线丝丝不断。麻很结实,以细为贵,细麻线是上品。疙疙瘩瘩粗粗癞癞的,谁要啊?
她要打麻了,就敲敲板壁:
“眉眉在不在屋里?过来帮我分麻。”
我就过去帮她分麻。
其实我们家也打麻,家家户户都打麻。但是象她们家有正规机器的不多。我姨妈下班了,黄昏时分,晚饭前后,拿一个小板凳那么大的竹制纺麻的轴,站在堤坡子上,拉长麻线不停地绞,全手工,不快。我只看热闹,帮不上忙。也有人笑话我,“看这个伢儿才好玩吧,自己屋子事不晓得做,去别人屋里帮忙倒跑得撅撅神。”
主要是分麻比较简单。可是老站着看机器吃麻,其实挺无趣的。我心早野到外头去了,机器还吭哧吭哧张着口不停地吃。怎么还没有打完呢,你不要写作业吗?我都站不起了。这还有好多麻呀。今天要打几个麻团?
她看我坚持不住了,就夸我道:
“你看你分的麻好细呀,这根特别好。”
我一高兴,又能站很久,两个脚换着抬起来一会儿,免得麻了。接着递给她一根麻:
“你看这根,这根好细。”
她就又说,“我们打的麻最好。是一等品。比别人都好。”
我就更高兴了。好象是我自己得了诺贝尔奖,获得全世界交口称赞。因为她说的是“我们”,我和她两个人。虽然奖金只归她一个人。可是荣誉啊。
但她有时候也说,
“不把这些麻打完,你不能出去玩。”
我望着那些麻,好多呀,这怎么打得完呀,到吃饭时候都打不完。奶奶怎么还不来叫我吃饭呀。我肚子都饿了。
她最不喜欢别人叫她“小酒瓶子”。因为她的名字里面有个萍字,又老要给她爸爸打酒。她一跟我吵架,我就叫她“小酒瓶子”。她气得脸通红,追着我打。我跑得快,她抓不住我。就算她抓住了,大人也会说她,你跟这么点小伢儿搞什么。她为了维护自己打麻能手的光辉形象,总是在街坊面前表现得特别完美。当然吵架归吵架,不久她又敲着板壁:
“眉眉在不在屋里?过来帮我分麻。”
.
.
.
3
跟我们这一排砖瓦房不相干,旁边歪歪斜斜搭着一个单独的砖头屋,似乎没有勾缝。是翠儿家。
翠儿比我大一岁,老在一起玩。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,她最小。两个哥哥一个叫和尚一个叫奶巴,都很奇怪很可笑。两个姐姐玉儿,珍儿。她叫翠儿。
她爸爸是水客,船上人,常年在江上漂,过年都不回来。后来回来就不走了,把房子修了一遍。她妈有些蓬头垢面的,不怎么出门。
她奶奶是讨米佬。要饭的,叫化子。
她奶奶并不常来。要饭要到这一片了,才进家里歇一歇。
可是她也并不歇着。一般都是杵着棍子在门口站着,高声叫骂。她说的乡里话,骂些什么听不大明白,大概就是指责媳妇怎么怎么不好,孩子怎么怎么不好,家里怎么怎么没有归置好。她骂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接嘴或者吭声。由着她骂。似乎不屑于理她的样子。又似乎觉得有个要饭的奶奶很丢脸。她从来不在他们家吃饭,更不在他们家住,有时候喝点水。痛痛快快骂一顿,骂完了就走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她奶奶也不在我们这里要饭,要走出很远,走几条街之后才开始要。街里街坊的,她给儿子留着面子。
翠儿家里跟别人都不同。花床单下面,没有棉絮,没有“绷子床”,铺的是厚厚的稻草。枕头里面装的糠麸子,睡上去会响。自己泡豆子发豆芽菜吃。家里成堆的白菜,从乡下拿来的。她姐姐掰一片白菜帮子,在地上划字。好象还拿米。乡下的新米比我们粮店供的陈米好多了。
翠儿本人却跟我,跟朋朋,跟文文,跟那边住的秋秋,跟所有的人,没有任何区别。
.
.
.
4
我们老在外面玩,疯。
官兵抓强盗。分两拨,一边是好人,一边是坏人。乱跑,尖叫。用手触摸到对方身体任何部位,对方就“死”了,蹲下,要等你的队友来救你。队友冲破重重阻碍,左奔右突妄想接近你,但是营救途中很可能自己也牺牲了,又蹲下一个。没关系,还有别的队友来救你,好好等着。救人也简单,跑到你身边碰一下,你就“活”了,重新站起来跑,又可以救别人。一般找根电线杆子或者一面墙当大本营,还要伺机跑回本营才算赢。
总有人不守规矩。玩着玩着吵起来。
“你都死了,我打到你了,你还跑!”
“没有。你根本没有碰到我。你来啦,你来抓我啦。”
“你痞了(耍赖)。你痞子!我明明打到你了,你死了,你要蹲下。”
……
“我不缠(理)你了。你太痞了!我不跟你玩了。”
“切,哪个跟你玩!你才痞,你最痞。我不缠你~~了。”
“哪个要你缠?我才不要你缠!”
“哪个要缠你?你个痞子!大河又没有哐盖子,你好去死去啦!”
“你去死!你本来就死了,还在这说么事说!”
……
我们玩“买羊”。选一个人当羊倌,一个人当主人,其余都当羊子。
大家手牵手一排,一边唱,一边往前走一步往后退一步。
羊倌:“走上街,走下街,叮叮铛铛敲金门哪,”
主人:“你是哪里人呀?”
羊倌:“我是岑河口的小羊人呀。”
主人:“你来搞么事的呀?”
羊倌:“我来买羊子的呀。”
这时主人来一句道白:“羊子还在洗脸。”后面的羊儿们急急忙忙两个手在脸前摸来摸去假装洗脸。
再来。
羊倌:“走上街,走下街,叮叮铛铛敲金门哪,”
主人:“你是哪里人呀?”
羊倌:“我是岑河口的小羊人呀。”
主人:“你来搞么事的呀?”
羊倌:“我来买羊子的呀。”
现在变成了:“羊子还在睡觉。”后面的羊儿们立刻闭上眼睛,假装打呼噜。
总之,主人随口瞎编一个什么,羊子们就都要照做,可以无穷无尽唱下去,可怜岑河口的小羊人就永远都买不到羊子了。
……
我们玩“求人”。分两拨,面对面,一拨进,另一拔就退。反之亦然。
“我们来求一个人哪,”
“你们来求什么人哪?”
“我们来求翠儿呀,”
“什么人来冲了吃呀?”
“就是我来冲了吃呀。”
然后翠儿就被“求”过去了。再归另一队开始求。这个也是循环往复,无穷无尽。从前有座山,山里有个庙,庙里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。讲的什么呢?从前有座山,山里有个庙,庙里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……
……
还有个无聊的儿歌,两个以上就能玩。边击掌边念。谁先笑谁就输了,憋着。同时拼命搞怪让别人笑。
“解放军,打敌人,
我们都是木头人。
不兴说话不兴笑,
笑了就是王八乌龟造。”
这些游戏,什么都不需要,有人就行。后来跳房子,跳橡皮筋,踢键子,翻绳花,抓沙包,则要一点物质基础了。
.
.
.
5
小孩子做游戏,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根本没有关系,有什么人,临时聚一起玩就行了。
“豁巴子”既想跟大家一起玩,又总觉得别人会欺负她。有其父必有其女,她的办法是先下手为强,老想欺负别人。
不管玩什么,每次都要她赢,否则就是欺负她。嘴又坏,总是说,“我叫我爸爸打你!”狐假虎威,狗占人势。
我们就对她唱:
“汽车来了我不怕,
我跟汽车打一架。
打不嬴,派爸爸,
爸爸是我的小娃娃。”
她说我,“娇娇宝贝十八岁,长大要枪毙!”
说翠儿,“你屋里是乡巴佬,你奶奶是讨米佬。”
说秋秋,“你没得妈,你没人要。”
时间长了,我们都不喜欢缠她玩。她觉得受了欺负,扬言告诉大人,要她爸爸来打我们。我们一起唱:
“娖奸婆,打赤脚,两个妈子象秤砣!”
她气急了,捡石头扔我们,对我们吐口水。我们一哄而散,没有还手。
以为这事情就过去了,小孩子家家的,吵吵架,又好了,是常事。但是我们第二天被她的爸爸王海生堵住,逼到一个90度夹角的山墙里,命令我们贴墙站好,他自己又高又壮挡在外面,太阳下巨大的影子投射到墙上,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。我们几个面面相觑,紧紧挤在一起,不知道他要干什么,心里很害怕。他从兜里拿出一把刀,在我们面前晃,凶巴巴地低吼:
“看到没有,我有刀。你们要是不跟XX(他女儿名字,实在不记得了)玩,我就把你们都杀死!”
我们有人叫了一声。他又吼道:“不许叫。”“你们要是敢告诉大人,我就把你们家大人也杀死。全部杀死!”
几个孩子吓得瑟瑟发抖,以为他马上就要开始杀了,不知道会先杀哪一个,他却转身走了。
我们又气又急,他是大人,他怎么能拿刀杀我们?又不敢跟家里说,怕他真的把全部人都杀了。他那么凶,别人都怕他。可是心里又咽不下这口气,只发恨再也不跟那谁玩了。各自闷闷地回家去。整个人仍沉浸在恐惧中。
翠儿偷偷告诉了她小哥奶巴,奶巴说要想个办法整整他们出气,一呼百应。而且奶巴不算大人。冬天下雪我们把长板凳翻过来当雪撬冲坡子的时候,都是他打头阵。
以前大家都用挂锁,铁将军把门。翠儿拿了根火柴,说塞到锁孔里,等他们回来打不开门,看他们怎么办。大家拍手叫好,立刻望风的望风,帮忙的帮忙,叽叽喳喳又怕大人看见了,快点快点。岂知锁孔并不是直的,里面弯弯曲曲,火柴插不进去。拿火柴的那个人一着急,火柴劈开,一小截断在里面。外面露着一点毛刺。大家傻眼了,以为会是一整根火柴在里面,他们要先拔出来才能开锁。管它的,就这样吧。
等他们回来,根本不知道暗中多少眼睛盯着他们开门。
王海生把钥匙插进锁孔,没能象平时那样打开锁,觉得奇怪,不由得加了几分力道。还是打不开,于是更加用力。他这一用力,就把那一小截火柴棍棍完全戳进去了。他女人抱着儿子不耐烦催着他快点,怎么搞的,门都打不开。王海生也不耐烦了,大声吼起来。女人将孩子放地上,一把推开他,自己去开,扭来扭去也打不开。我一开始躲在屋里探半个头出去瞄,觉得挺好笑的,后来就害怕起来,不敢再看了。王海生破口大骂,已经意识到被人做了手脚,血红着眼睛,感觉要杀人了。而且他骂什么不知道,变成了福建话,女人也高声大骂,相互指责,变成他们家独特的家常便饭的福建话对骂。王海生简直气疯了,手揪着锁将门乱摇乱耸,折腾了半个小时,最后,他从另一侧将门从轴上卸下来,才进去了。
我奶奶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不敢跟她讲。心里害怕,早早睡了。
那一晚隔壁特别安静。人高马大的异乡人王海生,被欺负了。本来他那么咋咋唬唬,喧声夺人,就是要让别人知道,他王海生不是好欺负的,你们有种上来试试,块头摆在那,又不是假的。他永远都不知道,他有本事欺负几个孩子,却也栽在孩子手里。
王海生点燃一支烟,回想当年背负多少期待和祝福才踏上这茫茫旅途,不禁仰天长叹,在风雨来兮的日子里,我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躲。
.
.
完整帖子:
- 沙头往事 第六章 上 - 眉子, 2016-04-26
![打开整个主题 [*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complete_thread.png)
- 坐沙发听眉子讲过去的故事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风华, 2016-04-26
- 风华, 2016-04-26
- 你还记得那句唱错的歌词吗,“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上面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。。”好毛骨耸然啊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6
- 眉子, 2016-04-26
- 谷堆,是谷堆,这样就不毛骨悚然了:)谁唱错歌词了呀?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风华, 2016-04-26
- 风华, 2016-04-26
- Here - 眉子, 2016-04-26
- 哈哈哈爆笑。 总记得萧亚轩的“你是我的猪大哥”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我为诗歌狂, 2016-04-26
- 我为诗歌狂, 2016-04-26
- 哈哈哈原来从这里来的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风华, 2016-04-26
- 风华, 2016-04-26
- 哈哈哈爆笑。 总记得萧亚轩的“你是我的猪大哥”。
- Here - 眉子, 2016-04-26
- 谷堆,是谷堆,这样就不毛骨悚然了:)谁唱错歌词了呀?
- 你还记得那句唱错的歌词吗,“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上面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。。”好毛骨耸然啊。
- 这篇读得过瘾。街头巷尾的百姓们似曾相识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丽桥游子, 2016-04-26
- 丽桥游子, 2016-04-26
- 风土人情,差不多吧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6
- 眉子, 2016-04-26
- 风土人情,差不多吧。
- 看得津津有味,非常有趣,呵呵呵。那个爸爸真是个蛮人,以为自己冲小孩子一抖狠,他们就会跟他女儿玩了?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我为诗歌狂, 2016-04-26
- 我为诗歌狂, 2016-04-26
- 他是抖狠抖惯了的,以为别人都怕他才好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6
- 眉子, 2016-04-26
- 他是抖狠抖惯了的,以为别人都怕他才好。
- 下班前赶紧上来把眉子的文看了,哈哈,官兵抓强盗好象我小时候也玩过,但没听过这个“哪个要缠你?你个痞子!大河又没有哐盖子,你好去死去啦!”“你去死!你本来就死了,还在这说么事说!” 哈哈哈,太笑人了。眉子细腻的笔触,把乡邻象白描一样清晰生动地描画出来,鲜活地象过电影,真的是拍电影的绝好素材。咱们客栈人要够多,演一出给你奶奶看多好。谁来演那个可恨的王海生呢?:)))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小活, 2016-04-26
- 小活, 2016-04-26
- 那是我们吵架的话,张口就来了,所有长江沿岸的人都会说这句话,“大河又没有哐盖子”,我在南京听到过。老姜会说福建话。哈哈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6
- 眉子, 2016-04-26
- 哈哈,话说这老姜片跑哪去了,让他咋唬吓人正合适:)))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小活, 2016-04-26
- 小活, 2016-04-26
- 看你能把他咋呼出来吗?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6
- 眉子, 2016-04-26
- 他可别出来亮菜啦,我第二天减肥,这次坚决要成功:P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小活, 2016-04-27
- 小活, 2016-04-27
- 他可别出来亮菜啦,我第二天减肥,这次坚决要成功:P
- 看你能把他咋呼出来吗?
- 哈哈,话说这老姜片跑哪去了,让他咋唬吓人正合适:)))
- 那是我们吵架的话,张口就来了,所有长江沿岸的人都会说这句话,“大河又没有哐盖子”,我在南京听到过。老姜会说福建话。哈哈。
- 这篇也是惊心动魄:))街坊邻里小人物的描写生动细腻,小孩子就是这样,我们小时候也是今天吵,明天好,放学一起游戏,简单而快乐:)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玉兰花开, 2016-04-29
- 玉兰花开, 2016-04-29
- 大人也都知道小孩吵架不算数,很少介入的。
![空帖子 / 没有文字 [ 没有文字 ]](themes/web_2.0/images/no_text.png) - 眉子, 2016-04-29
- 眉子, 2016-04-29
- 大人也都知道小孩吵架不算数,很少介入的。
- 坐沙发听眉子讲过去的故事